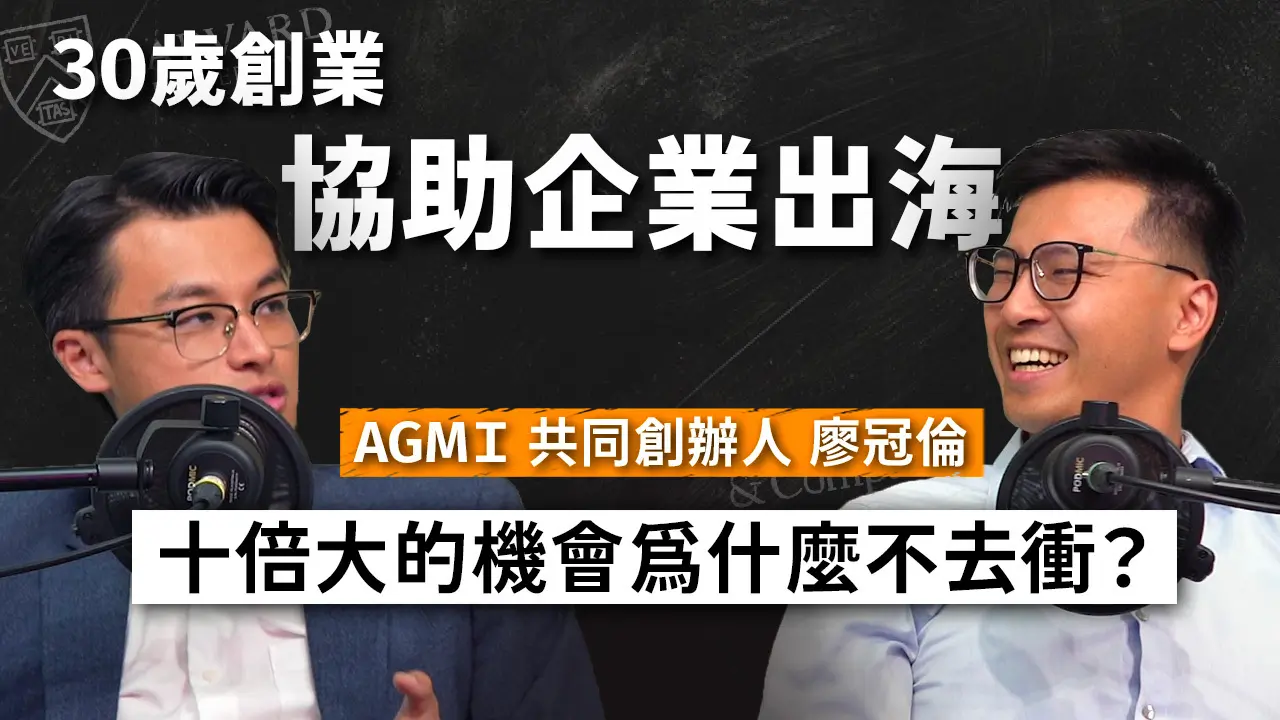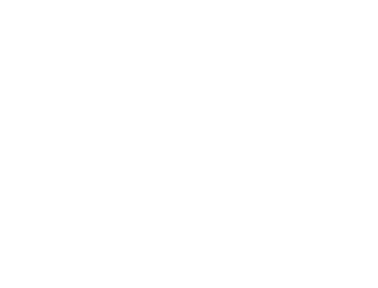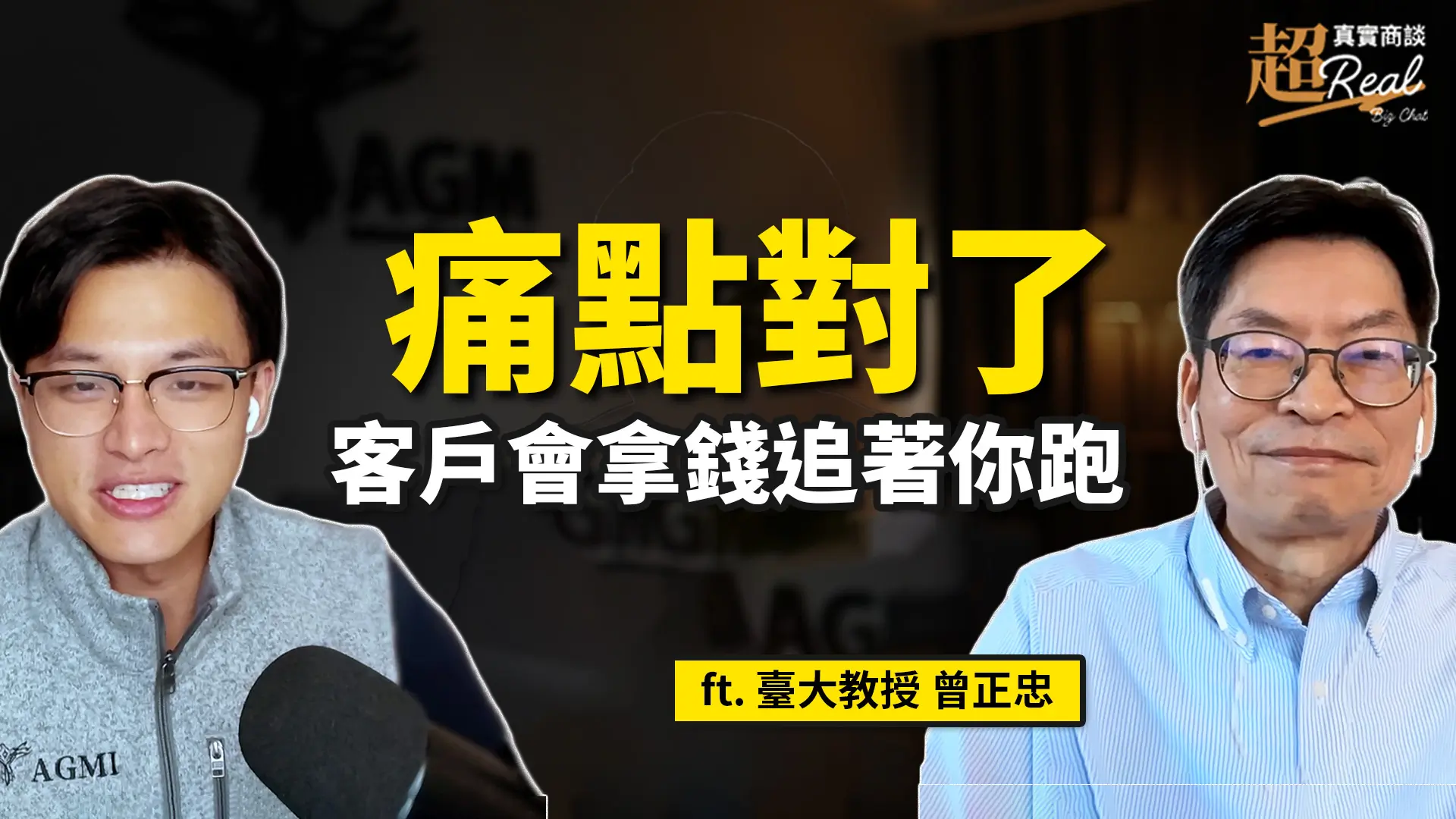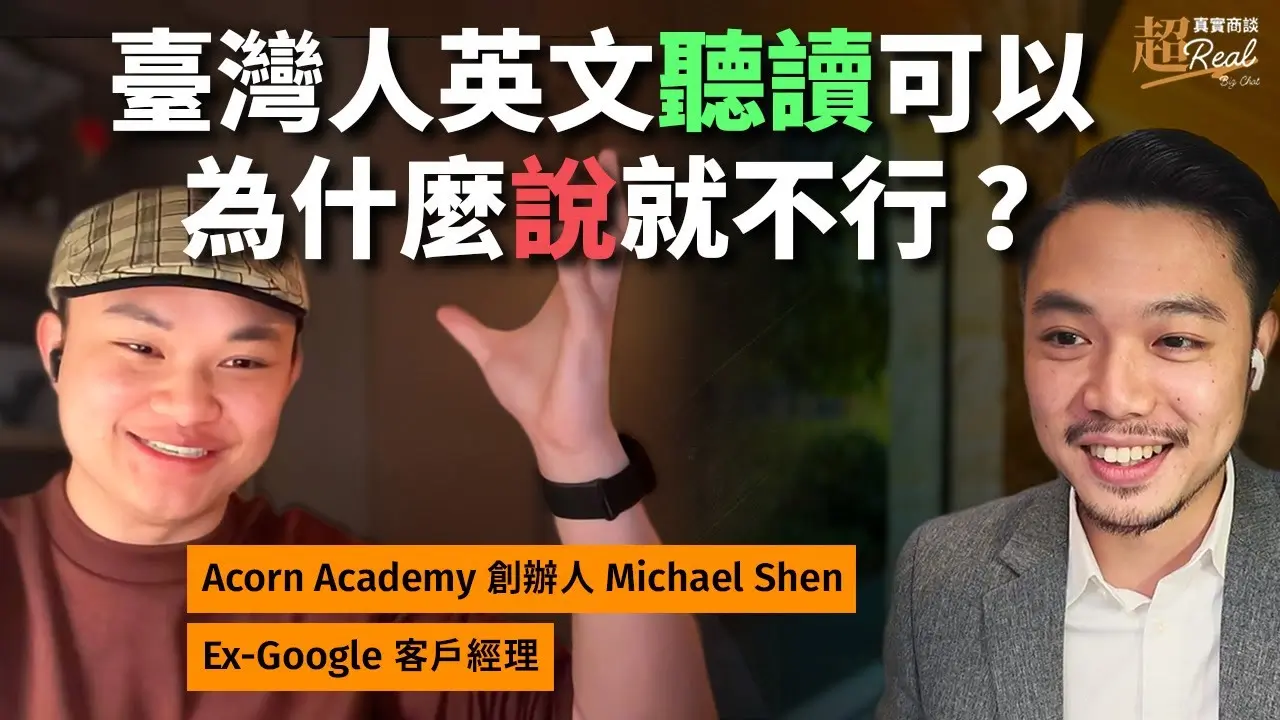Table of Contents
這次邀請到一位我認識了 20 多年的老朋友,也是現在一起創業的夥伴——冠倫。我們的緣分從國中時期開始,從那時起就一直保持著聯繫,直到現在一起創辦 AGMI Group,協助臺灣的 Deep Tech ( 深度科技 ) 新創走向全球。
這次的訪談中,我們深入聊了冠倫的職涯發展,他如何從科技業轉型進入創投,以及從創投的角度看待新創公司的成長與挑戰。我們也討論了 AGMI 是如何幫助臺灣 Deep Tech 新創突破資金困境,成功打入國際市場的策略。不論你是剛起步的創業者,還是正在尋找突破點的創投者,這場訪談都充滿了實用的經驗與建議,讓你更清楚如何抓住機遇,實現國際化。
▌關於廖冠倫
廖冠倫是 AGMI Group 的共同創辦人,擁有深厚的科技產業與創投經驗。他的職涯始於臺灣科技業,累積了豐富的跨國企業運營經驗。隨後,他前往美國杜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後又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 MBA ,進一步拓展國際視野。
在進入創投界之前,廖冠倫曾帶領數家 MedTech 與 Climate Tech 領域的創業公司,成功幫助它們從早期階段迅速成長並打入國際市場。後來,他在矽谷、紐約和歐洲的創投機構中進行投資,聚焦於人工智慧和金融科技領域,並以天使投資人的身份支持早期新創。
除了創投業務外,廖冠倫還負責管理家族辦公室 ( family office ) 的資產,為其構建了多元化的投資組合。他在資產管理與創投領域的豐富經驗,也為 AGMI 帶來了強大的專業背景,幫助臺灣的 Deep Tech 新創企業實現國際擴張。
以下是我們的對談內容:
開場介紹
Harvey:
哈囉大家好,我是 Harvey。這一集很高興邀請到我的創業夥伴冠倫,也就是 AGMI Group 國際的共同創辦人。
我們認識超過 20 年了,一路從學生時代鬥嘴打鬧,到現在一起經營公司。這段歷程非常特別,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們一起創業的一些契機與觀察。
冠倫: 大家好,我是冠倫。我從交大畢業後在科技業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去 Duke ( 美國杜克大學 ) 修了一個碩士,後來因緣際會回到臺灣創業、募了三百多萬,再去美國念了 MBA,接著進入創投,最後跟 Harvey 一起創辦了 AGMI。
踏上矽谷的文化衝擊
Harvey: 你覺得到矽谷,最讓你有文化衝擊的東西是什麼?
冠倫: 我第一次到舊金山是 COVID 後不久,當時整個城市混亂的狀況讓我滿震撼的。我那時候唸柏克萊,附近有一個公園叫 People’s Park —— 裡面至少四、五十個帳篷,流浪漢聚集、藥物氾濫,其實這些都是灣區繁華之下不為人知的一面。
Harvey: 在舊金山生活,到底有多貴?
冠倫: 如果在舊金山市區要跟別人合租一個兩房一衛,至少要四、五千美金,車位一個月也要三、四百美金。出去吃飯,基本上要 10% 的稅加上 20% 的小費,隨便一餐都六百多臺幣。
Harvey: 那你有沒有什麼推薦的舊金山的食物?
冠倫: 那邊的亞洲料理是真的蠻不錯的。墨西哥料理也不錯,但可以吃到好吃墨西哥料理的地方,環境都不會很好、不太安全,要鼓起勇氣結伴去吃。
我自己剛到美國的時候,最喜歡去的地方是 Costco。那邊的熱狗堡只要 1.5 美金,跟臺灣的價格一樣,推薦給各位。
為什麼還是選擇去矽谷?
Harvey: 說真的,舊金山又亂又貴,但很多人還是選擇去那邊發展,你覺得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冠倫: 因為那邊的人脈跟你的生活圈吧。那邊總是有各式各樣的交流活動、展會等,你只要去參加就可以認識很多厲害的人。當我們把一個點一個點連起來的時候,人脈網可以創造出來的價值就可以很可觀。
再來是天氣真的太舒服,白天 25、26 度,晚上 18、19 度,穿著 T-shirt 走在外面是不會流汗的。
Harvey: 冠倫真的是我認識社交能力最強的,沒有之一。改天應該來錄一集「怎麼在國際場合主動交朋友、認識潛在投資人或客戶」,我們有的客戶就是冠倫去會場隨機聊聊出來的。
臺灣創投 v.s. 美國創投
Harvey: 蠻好奇你怎麼會選擇走上創投、投資這條路?
冠倫: 一開始會接觸到創投是因為那時候在創業,基本上所有的新創公司都需要募資,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跟創投、跟天使投資人聊。
因為臺灣的創投之中,很多都是財務型的投資人,對於你的技術他們可能不懂,但他們很重視財務數字。就算你連產品都還沒有,他們還是會問你說,你預計一年之後、五年之後,可以賺多少錢?
後來我有機會到矽谷那邊做創投,當然那邊在追求的一樣是財務型的回報,但是大家會更重視你這個團隊有沒有辦法去真的去把你說你想要做的這個產品做好,以及為什麼你是一個適合做這個產品的創辦人?這就是所謂的 Founder-Market Fit ( 產品市場契合度 )。
Harvey: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悖論 —— 你連產品都還沒出來,怎麼可能做出很精確的財務模型?我們自己平常也會建模型,所以知道裡面變數超多。只要稍微改一個參數,最後整個數字就會差很多,所以我會說這種情況叫 False Precision ( 假精確 ) ,看起來好像很準,但根本不可能準。所以如果投資人想依賴一個數字來做決策,其實就會有很多限制。
冠倫: 像我們的大哥 —— Twitch 的 Co-Founder Kevin Lin,他說他當年建的模型預測最後還真的很準,但那根本是千萬分之一的幸運。
Harvey: 沒錯。而且我們在建財務模型的時候,常常就會假設一路往上走,很多人模型裡都會寫說營收每年都一直成長,但實際上是可能第一年有錢、第二年歸零、第三年才又頂上來。
冠倫: 在美國,很多創投合夥人自己是創過業的,所以他們的整個思考模式就不一樣。因為如果你有走過創業那條路,就會知道建這些財務模型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重點是你怎麼把產品賣到理想的客戶手上。
創業的關鍵不是技術,而是市場
冠倫: 像臺灣的生技、醫材新創,很多創辦人本身是中研院或大學教授,技術很強但不一定有市場觀念。矽谷其實反過來,很多時候產品還沒開發、甚至根本還沒有技術,就會先去跟客戶聊、去了解市場到底有沒有真正的痛點,然後再決定要不要繼續做下去。
痛點有分兩種,可能是被蚊子咬、可能是被鯊魚咬 —— 如果你今天被鯊魚咬了,你就會想辦法、用盡你的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但如果你今天只是被蚊子咬,這個痛點就沒那麼痛。要去找到真實的痛點,而不是從技術這端出發去說「欸,我有一個很好的技術」。
Harvey: 光是要確定有需求,就可以花很多時間,但也完全值得花這個時間,不然投入好幾年、砸一堆錢做出來,結果市場不買單,我們看過好多案子都是這樣,真的太可惜了。
冠倫: 對,所以在美國一些頂尖的加速器,例如最知名的 Y Combinator,每個團隊都要做超過 100 個用戶訪談、去聊他們的痛點與需求,不斷 Pivot (調整方向) 。而臺灣很多團隊則是會埋頭做技術,最後才在找客戶與市場。
Deep Tech 新創的市場挑戰
Harvey: 我覺得這種狀況在「Deep Tech ( 深度科技 ) 」領域特別明顯。
「Deep Tech」就是你需要投入大筆時間與金錢去做的技術,例如火箭、生醫新藥研發。因為本來就預計未來幾年內都不會賺錢,所以驗證需求這件事常常會被大幅度滯後,畢竟不管有沒有去驗證,都要幾年後才能開始賺錢。而且這種 Deep Tech,當你整個花時間、做下去之後,你已經很難 Pivot 了。
要講 Deep Tech 的話,很經典的例子就是 Elon Musk 的 Space X 火箭。他說 Space X 未來想要商用,一般人只要付得起那個錢,他就帶你上太空 —— 技術是新的、市場也是新的。
而像醫療器材好了,醫院沒有你這個新器械,還是有解決方案 —— 就是醫生的手。你要讓一間醫院換用你們的新器材,不只技術要好、要說服醫生,還要讓醫院 IT ( 資訊部門 ) 、採購、合規部門都同意,這種 B2B ( 企業對企業 ) 流程非常複雜。
這種時候,如果東西賣不出去,到底是因為市場沒有這個需求,還是是我不會賣這個東西、沒有進入 B2B 銷售流程?
創投如何評估創業團隊、創業資金來源
Harvey: 冠倫你在做創投或做天使投資的時候,會怎麼評估一個創業團隊值不值得投資?
冠倫: 我們通常不會去投連產品都還沒有的,因為這個對我們來說風險實在是太高。
創投有分幾個階段:最早期有些所謂的 first check,它就比所有的機構投資人都還要更早,在賭的就是這個創辦人有沒有辦法去把他們的產品按照他們的想法執行出來。再來的話就可能到 Seed 或者是 Pre-Seed,這種種子輪的時候基本上有一個 MVP ( 最小可行性的產品 ) 了,可以用這個產品去跟客戶做介紹,但是它還沒有辦法被放大到商用,我們在看的案子通常都是在這個階段。
資金的部分,創業通常就是靠「三個 F」來支持你 —— 第一個就是你的 Family 家裡,可能你一些親戚會不會認同你的想法;再來就是你的 Friends,要有辦法讓周圍這些這麼親近你的人被你說服,你才有可能去說服外面的機構投資人;最後一個 F 其實就是 Fool,就是所謂的傻子,他們其實扮演天使投資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角色,這些 Fool 他們在天使投資其實可能創造上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回報。
Harvey: 後期精打細算半天,不如早期選到對的人。在很多經典的矽谷創業成功故事裡面,當主角去找第一筆投資的時候,就是什麼都沒有。像那時候孫正義投資馬雲,他說原因就只是因為馬雲的眼睛很有神。後來孫正義這個投資,賺了幾千倍的錢。
創投如何看待 Portfolio ( 投資組合 )
Harvey: 我們剛剛講到,最前期的早期天使投資人絕對是全有全無這樣。但當你站在 VC ( 創業投資 ) 機構投資人的角度,你們會怎麼去想 portfolio 這件事情?
冠倫: 矽谷前陣子被詬病的是,很多的機構投資人都是在做一個所謂 spray and pray,把錢撒下去之後就開始祈禱。所以大家也開始重新回來思考說,我可以怎麼樣更好的去建構我的 portfolio?
我們前陣子有看到一些創投,他們就沒有要追求幾百倍的回報,而是追求一個穩定的兩倍到三倍,那基本上在投的可能就不是非常非常早期,而是已經看到產品,甚至已經看到一些早期的 市場成績,就是已經有一些客戶願意購買這個產品,這個時候他們才會進去。那這個產品可能沒有辦法變成一個獨角獸。現在開始有一些創投是走向這個方向,比較審慎的去看待市場。
Harvey: 這是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一個蠻大的變化。因為一般我們會來講說,作為早期投資人會希望你的案子有百倍的可能性,但實際上這很難達成。畢竟投資就是投資、賺錢就是賺錢,也許他沒有長成獨角獸,但是有賺錢,那也好嘛,不一定說這個東西沒機會變成獨角獸,我就不投或者就不認真去看。我覺得過去幾年大家開始變得更實際,是好事啦。
臺灣與美國募資環境的差異
Harvey: 很實際的就是,你要開公司就是要募資。冠倫,以你的經驗,你覺得在臺灣跟在美國要成功募資,最大的差異會是在哪裡?
冠倫: 我覺得這個要回歸到資金在哪裡。基本上臺灣握有資金的人,很多都是所謂傳產的老闆,他們對於現在新的這種 SaaS ( 軟體即服務 ) 其實沒有很能理解,選擇投資的大部分都還是比較保守的、有形的一些資產。但在美國,基本上這些創業家可能除了傳產之外,很多都經歷過過去的網路時代,他們知道說這個是會成功的,所以他們就願意來支持新一輩的年輕人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根本上面就是,臺灣有錢的人可能對於投資新創這件事情沒有這麼大的熱忱。但在美國,他們整個這個生態系已經比臺灣完整太多了,他們會有源源不絕的新點子,然後也會有一些資金願意支持。
在臺灣募資還有另外一個侷限是:臺灣本身的市場小。臺灣兩千多萬的人口,跟美國三億人口相比,當然是要瞄準海外市場。臺灣的點子搬到美國去的話,你可能可以用十倍的估值募到這樣的一個資金。
募資的困境與挑戰
冠倫: 如果你沒有辦法用漂亮的估值去募到一筆資金的話,早期的時候可能你的股權就會被稀釋掉。因為每一輪在募資的時候,你會不斷的拿你的股權出來跟你的投資人換錢,所以你身為一個創辦人的股權就不斷被稀釋。等到最後,甚至你要把公司賣掉的時候,可能你這個創辦人根本一毛錢都拿不到。
前期你怎麼樣去把你的估值,很強而有力的去說服你的投資人,告訴他說你的公司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價值,這件事情其實蠻重要。現在這也是臺灣很多新創公司碰到的一個難題 —— 你早期資金不夠,沒有那個談判籌碼可以去跟投資人去談說我想要比較好的估值,所以就只能將就你拿到的投資條件書 ( Term Sheet )。
在美國的話,基本上不好的案子就募不到錢,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不錯的團隊加上不錯的想法,你整個發展的空間會比在臺灣還要廣闊很多。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政府跟很多新創,他們從第一天開始就會想要往美國發展。
Harvey: 其實現在資訊很普及,各種資訊出來的時候,所有人接觸到的時間點會差不多。也就是說,在臺灣你想到某個創業題目的時候,大概率在美國某個地方的某個團隊也會想到差不多的東西,但純粹就只是因為市場的差異,導致你們做一樣的事情,市場估值卻差十倍以上。
我自己 25、26 歲發現這件事的時候,就決定換個環境去美國看看。
想打美國市場,你要準備好什麼?
Harvey: 如果你今天在臺灣,想要瞄準美國市場,有哪些事情要先去想?或是在你的經驗裡面,最常看到大家會低估困難度的事情是什麼?
冠倫: 第一個是,「文化」會影響到你的產品。例如金融市場,臺灣的金融法規跟美國的金融法規是完全不一樣的。另外,像臺灣可能現在才慢慢開始接受行動支付,但在美國大家都已經很習慣出門不帶現金,這種文化根本上的差異,會影響到你產品的需求。
如果你真的想要瞄準美國這個市場,要嘛你就找一個當地的共同創辦人,要嘛自己到美國實際生活一陣子,實際上跟當地人互動、去了解他們是不是有這樣的需求。這件事情的成本很高,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很多臺灣新創走不出臺灣,因為你前期就是需要花這麼大的 心力。
很多新創覺得,去參加一些展會就有辦法建立一些連結,但沒有思考到的是在去之前有很多功課要做。你要了解去參加這些展會的人是誰 —— 如果你去參加一個展會,所有人都是賣家,但你卻去那邊找買家,基本上對你公司的效益大概就只有在臺灣的報紙上,可能有曝光說這個臺灣團隊到海外參展。
SkyDeck 與落地美國的新路徑
冠倫: 現在臺灣的技術底子跟臺灣人才,其實是有被國際市場看到的。
柏克萊那邊有一個叫 SkyDeck 的加速器,慢慢有開始收越來越多的臺灣團隊,在那邊幫他們落地、幫他們成立美國的公司。這些加速器前期可能會給一些資金,也可能不會,但至少可以把你的人放在美國環境,你周邊的人就是一些想打美國市場的創業家,你們可以彼此交換資訊。這些加速器通常會幫你安排一些有經驗的業師、幫你找到適合訪問的對象。這樣其實是對於臺灣新創在美國落地有蠻大的幫助。
因為過去幾年,不管是臺灣人自己努力,或是政府資源的一些挹注,海外慢慢開始有加速器願意去接受臺灣團隊,然後臺灣團隊也很勇於嘗試。
Conference 不一定有用,關鍵人不在展場上
Harvey: 我們前面講到,你要把東西賣出去,要處理非常多細節。雖然很多人有概念說,要往美國市場走,我必須人要過去、要去參加展覽、要去跟美國客戶聊,但實際上成效還是不好。那包括幾個原因,像剛剛講的展會問題,事實上就是那樣。
因為會在展會旁邊顧攤位的人,都是賣家。實際上的買家、關鍵決策者,根本不會出現在展會裡面。他們在哪裡呢?每次展會旁邊都會有很好的飯店,通常比較認真的買家,會跟一些人在會議前就先聯絡好了,然後他就在展會旁邊飯店的高級會議室裡面,一天開好幾個會,全部一起見、一起聊。所以你在展會上面,遇到真的能對你的公司帶來很大幫助的人的機率,真的不高,不是一個很有效率的人脈建立方式。
創業的重要觀念:時間就是成本
Harvey: 大家要記得一個觀念是:你的時間是很寶貴的。
我們剛剛講到臺灣跟美國公司思考事情的差異,其實還有一個很根本的差異是,在美國大家很習慣「術業有專工」、不同領域有不同專家的概念。所以當有專家、顧問,該付的錢就是付。比起省那個錢自己去想辦法、這邊撞撞那邊撞撞,不如直接找個專業的人來,幫你省下許多時間。這個很核心的差異其實也在於,美國人均收入相對於臺灣高很多,所以對於自己的時間也會覺得更珍貴。
所以,特別是新創公司,要記得你的時間就是很寶貴,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一下就過了。
給想走向美國市場的團隊三個建議
Harvey: 我想問冠倫,如果你可以給想往美國市場走的團隊三個建議,你會給哪三個建議?
冠倫:
第一個,也是最容易執行的,大概就是找到好的顧問。如果你找到已經對美國市場很了解,同時又是你這個領域的人的話,對整個團隊的幫助會非常非常巨大。為什麼需要顧問?如果你的團隊都陷在同一個小圈圈裡面、大家都覺得這個方向非常好的時候,你需要有一個德高望重的人來告訴你,這件事情可能沒有你們想像中的這麼好。我們自己的一些事業,我們請的顧問就直接告訴我們說:「What the fuck are you guys doing?」所以這件事情就是需要有一個當頭棒喝。
第二個是,往美國市場是大家都想瞄準的一個方向,但現在其實整個東南亞,所謂新興市場,其實也是充滿機會。印尼、越南,這些市場他們本身的文化可能跟臺灣比較相近。所以如果你的產品本身本來就比較適合亞洲群體的話,你公司可以設在美國,但鎖定亞洲市場。美國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生態系,但你要競爭的可能就是 Stanford、MIT、柏克萊、哈佛的這些頂尖人才。那如果你往東南亞走的話,以臺灣人才的素質,很可能是可以獨霸一方的。
第三個,很多臺灣人其實不知道,美國其實有一個創業的簽證。大部分人會想說,我一定要去念書,才有辦法拿到工作簽證、才有辦法留下來。但其實美國有一個叫做 O1 的簽證,基本上這個簽證是三年,是申請制的。
AGMI 的創立初衷:讓有價值的知識可以被更多人利用
Harvey: 我們會出來創 AGMI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一路上也受到很多前輩的幫忙,還有我們發現要在美國真的落地、打出成績,要顧的細節非常多、成本非常高、溝通非常困難。如果期待自己從頭開始摸索,期待可以自己弄懂全部的事情,這個機率其實有點低。
麥肯錫的收費非常非常的貴,但是那個服務對客戶有沒有用呢?是真的非常非常有用。因為你直接補上了一個人家完全不知道的知識鴻溝,而且這塊知識鴻溝可以給別人帶來成果。
那我在麥肯錫的時候,看到這個情況,我心裡想的是,這個服務對大部分的臺灣公司也很有幫助,但他們付不付得起麥肯錫這個錢?百分之一千付不起。
我那時候就打給冠倫。我們有沒有辦法把這樣的東西做成一個事業,然後幫助到更多臺灣團隊?AGMI 最早最早的發想、契機,就是從那個時候來的。
一起創業,是因為信任與共同願景
Harvey: 我蠻好奇,那時候我跟你講這個想法的時候,你的想法是什麼?
冠倫: 那時候我想說,OK,我們之前一起做了這麼多奇怪的事情,終於要來做一些正事了。
一路走來,從國中認識到現在,Harvey 都是我覺得我很佩服的一個人。之前 Harvey 找我投資很多東西、玩各種東西,我從來沒有跟 Harvey 說過「不」。因為對我來說,我不是在投一個項目,而是在投資 Harvey 這個人。這跟創投其實很像,大家沒有辦法去預測未來,投資的真的都是這個人到底適不適合。
那時候 Harvey 來找我,我覺得我第一個想法就是,做事會非常非常愉快。很多人說不要找自己的朋友一起創業,但我自己覺得,找你很好的朋友一起創業,你們才有辦法很務實的去溝通。因為你們有很紮實的友情當作你們的基底,所以不會因為你講了什麼誠實的話,你們就慢慢漸行漸遠。
另外就是,因為 Harvey 提到說,他想要幫臺灣公司有辦法出海,那結合 Harvey 在顧問業的經驗跟我之前在創投界的經驗,一定有辦法幫助到一些團隊。如果我們能夠幫臺灣團隊真的走出海、在國際舞臺上發光發熱,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有成就感。
為什麼放棄高薪創業?因為值得一搏
冠倫: 當時在 Harvey 說「要不要一起來創業?可能沒有錢」的時候,其實有另外一個創投說「要不要過來?這邊有不錯的薪水可以給你」。我綜合評估之後覺得,還年輕嘛,30 出頭,創業這件事情是值得放手一搏的。
Harvey: 必須說開 AGMI 之後,好像沒有比較輕鬆。作為專業的服務性公司,客戶半夜 1 點打來我家,我也是會起來接的。
冠倫: 沒錯,同時又要管理美國跟臺灣的時差。
不只幫臺灣,還想幫整個亞洲團隊出海
Harvey: 剛剛冠倫有講到,我們是希望回來幫助臺灣的公司,或者把範圍稍微放寬一點,幫助亞洲的公司。
我那時候會這樣講是因為,我自己在麥肯錫的時候發現,也不是只有臺灣人,日本、韓國最頂尖的就是哈佛、MIT 都 PhD 念完了,然後進了麥肯錫,但其實他們在職場適應上面都會有一段陣痛期。如果哪天他們要在美國自己開公司,也是會有那個陣痛期存在。
那我們自己這樣撞來撞去,也累積了一些經驗值,還有包括我們身邊一些很照顧我們的前輩,其實可以幫大家很有效的去把這段陣痛期給縮減。當然有的該受的傷害,要自己受過才會長大,但我覺得我們作為自己走過這段路的人,可以很有效去避免一些明顯的錯誤點,讓大家這條路走得更順。
我那時候決定要做這件事情、離開麥肯錫,很大一個原因是,我發現我每天很認真工作,都是在幫美國老闆賺錢。那如果我們今天都可以幫美國的老闆、幫美國團隊賺錢,為什麼我們不能回來幫臺灣老闆、臺灣團隊賺錢?對我們來講,回來幫臺灣做這件事情,就是剛剛講的那個額外的成就感,畢竟對這塊土地是有很大的認同感在。
這就是為什麼我的 Youtube 頻道叫「Dr. Harvey 不廢話」,我們每次提供任何建議或提供任何服務,都會換個角度想到底有沒有用。現在大家其實是完全不缺乏資訊的,如何在正確的時間點給你正確、你可以消化的資訊量,並且能讓你採取行動,才是最後可以導致結果差異的地方。所以我和冠倫在 AGMI 會一直去推說,這東西對客戶是不是真的有用、有幫助,能不能帶出他們真的要的成果。
那也是為什麼剛剛會跟大家分享說,我覺得不管自己做生意或是你想要創業成功,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 如果有東西,尤其是經驗,你可以用錢買到,你就絕對是用錢買經驗,因為你要自己去轉完之後再學到那個經驗的成本,絕對更高。這個概念有的話,很多時候你去評估自己的時間成本、去評估其他人的時間成本的時候,會有更清楚的概念,人家也會更願意跟你合作。
AGMI 到底在做什麼?
冠倫: 那 Harvey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所以 AGMI 在做什麼?
Harvey: 好,其實我們 AGMI 在做的事情,就是剛剛講的,我們想要幫亞洲人才,特別是臺灣人才跟公司,站上國際舞臺。
人才的部分要怎麼實現呢?就會透過很多培訓課程、活動,還有我們的一些計劃項目來實現。今天這集跟大家聊的比較是企業端,那企業端可以簡單想成我們是家教班,這間公司如果對你很重要,就很像你以前大學聯考想要考到很高的分數,你會去補習或找家教,因為那些人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在 AGMI 這邊,我們等於是掌握了亞洲企業出海落地到美國,中間所有的細節、環節,從你的公司設立、股權結構,一路到落地的客戶開發、拓展人脈關係、當地的運營維護,還有資金營運上面的建議。我們就是想要創立一個公司,可以把這整段的東西都包起來。
我們服務的客戶類型很特定,主要就是服務比較偏科技相關的公司,包括 BioTech、CleanTech,跟剛剛講的一些軟體類型的公司,這種本身比較有技術含量的公司。
那我自己的背景是醫療相關,所以我就是在做醫療相關的案子。冠倫則是帶著他投資人的角度,站在客觀第三方告訴我們的客戶,如果想要吸引投資人支持的話,怎麼做會最有機會。很多時候吸引投資人,其實就是你把你的公司變成一個更好的公司,就會吸引到投資人。
冠倫: 這邊剛好可以補充一下,臺灣的公司其實有很多底子非常好的公司,但他在陳述他的故事的時候,他只能講大概 10、15 分。但在美國,很多不怎麼樣的公司,他可以把它講成 100 分。這個說故事的能力,所謂的商業敘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Harvey: 這也是我們 AGMI 一個主要的服務,我們會幫這些公司想出他們最棒的商業敘事,讓這些投資人、客戶可以更正確的理解到他們的價值,更有機會去跟他們合作或是投資他們。
Harvey: 今天很感謝大家花時間跟我們聊聊這些重要資訊。
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認同這個理念,認同說希望臺灣公司跟人才可以走上國際舞臺,或是你公司本身有在想出海這件事情的話,歡迎寄個 email 跟我們打個招呼,我們都很高興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那我們這集節目就到這邊!
冠倫: 大家掰掰!
Harvey: 掰掰!
▌關於 AGMI Group
AGMI Group 專注於提升生技醫療、永續科技及工業製造領域的企業發展。我們的核心使命是透過提供全方位的商業解決方案,幫助客戶達成增長目標。業務內容涵蓋資金募集與商業敘述、新市場銷售及行銷策略、系統化國際商業開發及授權、企業投資組合策略、商業盡職調查及投資出場策略。
我們結合深厚的技術見解與行業專業知識,為客戶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持,重點解決企業在邁向國際市場過程中遇到的挑戰。我們不僅關注企業的短期增長,更專注於確保客戶能夠在全球市場中實現長期、可持續的成功。
🦅 官網:https://www.agmigroup.com/
🦅 聯繫我們:info@agmigrou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