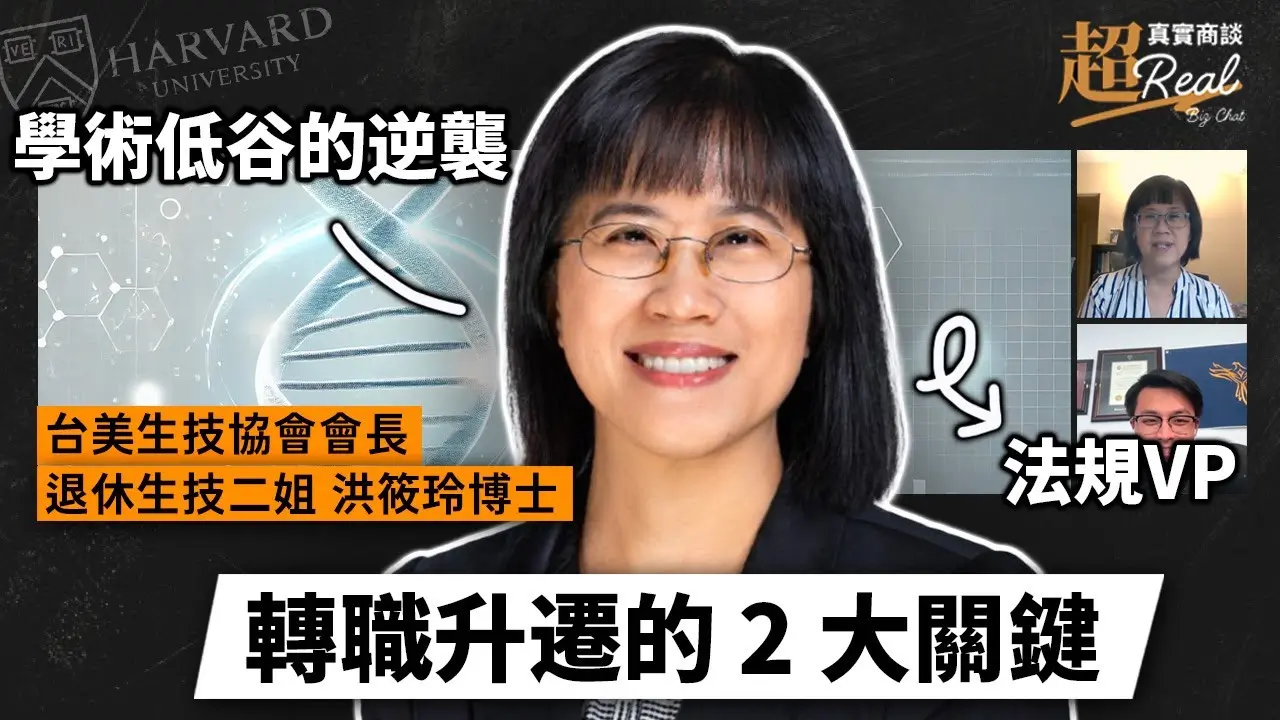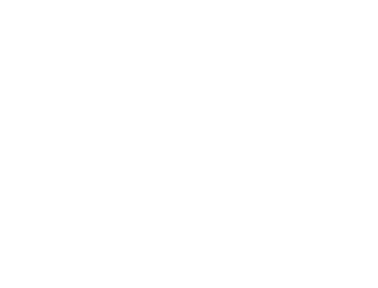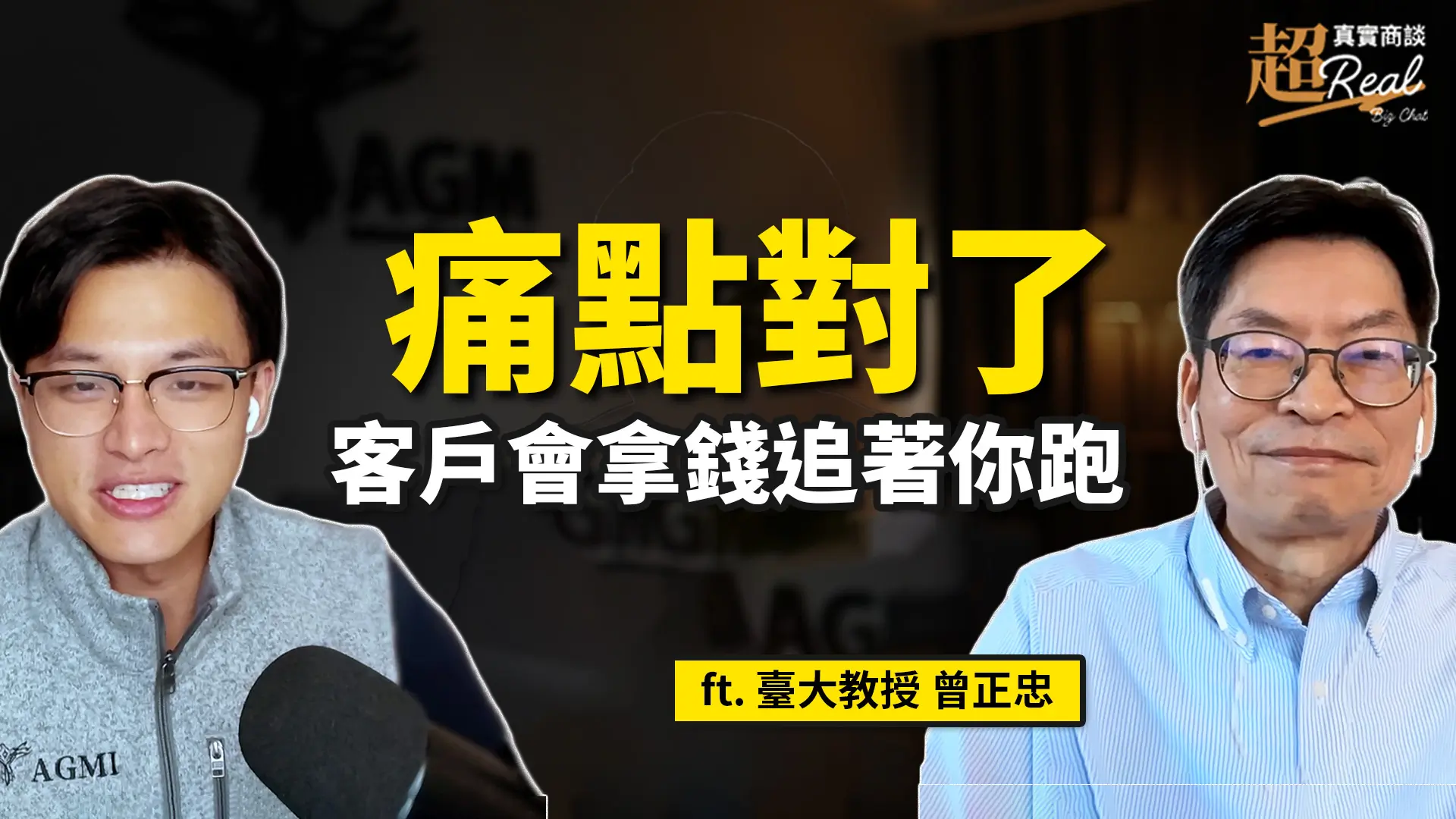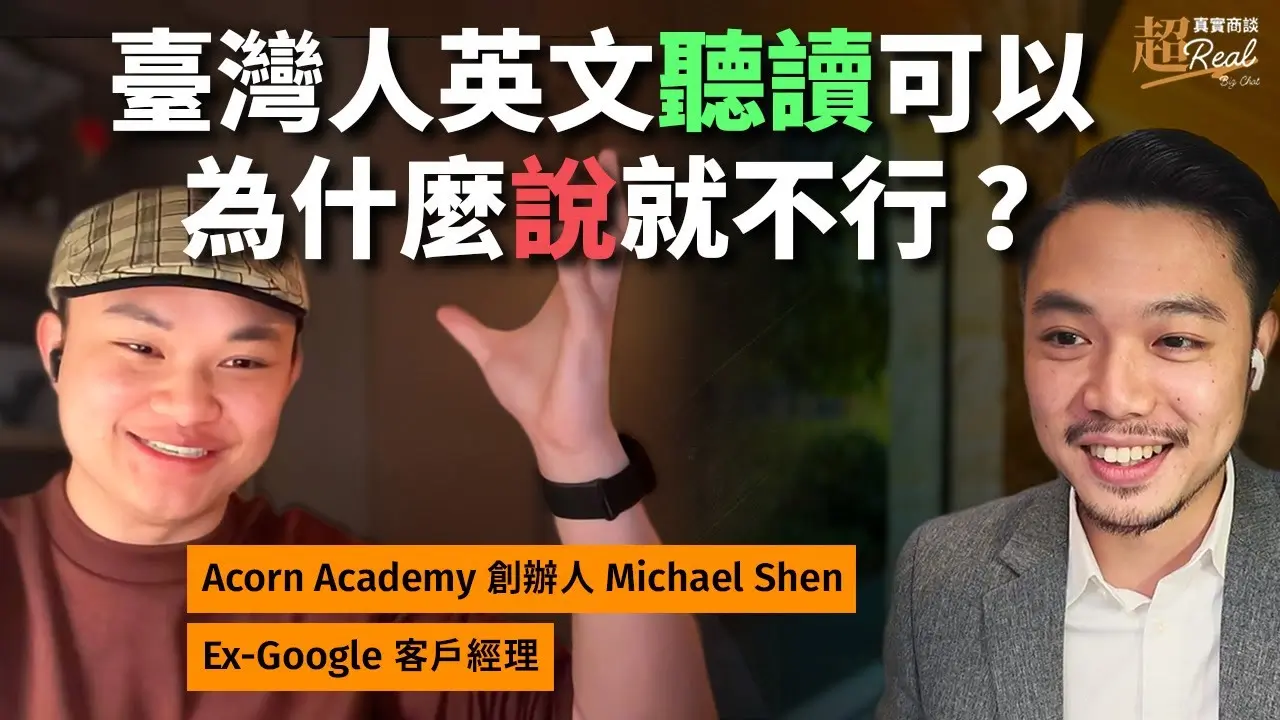Table of Contents
今天的訪談,我們邀請到了一位重量級來賓:現任台美生技協會會長,也是粉專有萬人追蹤的「退休生技二姐在美國」洪筱玲博士!
訪談中,我們聊到:
- 學術夢碎後的抉擇:從 43 歲學術夢碎,到製藥業界的高層法規專家,她如何在生技產業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 法規專家的養成:為什麼製藥法規是生技產業的關鍵角色?
- 低潮中的轉念:失業時她做了哪些選擇,如何應對失業、面對低潮,改變了人生?
- 女性職場突破:她如何在製藥業界突破性別限制?
- 職場必學關鍵技能:如何溝通、爭取升遷,主動掌握人生!
她用自身的經歷告訴我們,學術界到業界的轉型雖然困難重重,但並非不可能。無論你是對生技業有興趣,還是在職涯低谷中尋找方向,這次訪談都會給你滿滿的啟發與能量!
▌關於 洪筱玲博士
洪筱玲博士是生技與製藥界的重量級人物,現任台美生技協會會長,專精於製藥法規與品質保證領域。她曾在多家國際頂尖大藥廠 ( 如 JNJ、BMS ) 擔任高階職位,帶領團隊完成多項新藥開發與監管挑戰,作為業界少數能夠與 FDA (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 高效對話的法規專家。從學術研究到業界的成功轉型,洪博士的故事充滿啟發性。她不僅突破了學術與業界的隔閡,更在職涯低谷中找到方向,進一步奠定了她在生技法規領域的地位。退休後,洪博士透過臉書粉專「退休生技二姐在美國」,積極分享職場經驗,幫助生技領域的年輕人才找到職涯突破的契機,並推動臺美生技交流合作。
洪筱玲博士 LinkedIn:https://www.linkedin.com/in/hsiao-ling-hung-phd-rac-7771113
以下是我們的對談內容:
開場介紹
Harvey: 哈囉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 Dr. Harvey 的頻道。
今天的來賓是非常照顧我們的前輩,她曾經擔任美國安博生物 ( Ambrx Inc. ) 的法規事務與品質保證資深副總裁,也曾在 JNJ、BMS 等大藥廠擔任法規總監。看起來是非常成功的職涯,但其實她也經歷過幾次求職失利,直到 43 歲才從學術研究轉行到業界。在短短十幾年間,她就在美國製藥的法規領域闖出名號。今天,我們要來聊聊她的職涯故事,讓我們歡迎現任台美生技協會的會長、江湖名號「退休生技二姐」的洪筱玲博士,筱玲姐好!
二姐: 大家好,我是二姐。
關於「退休生技二姐」粉專
Harvey: 二姐有一個破萬追蹤的粉專,我自己很喜歡看,叫做「退休生技二姐在美國」。其中,我特別喜歡粉專的介紹:「一哥一姐在忙,二姐教你」,我看一次就記得了。
想請問你當初是怎麼開始寫粉專的?一開始有設定是給哪一群人看的嗎?
二姐: 我當初會開始寫粉專,是因為剛退休,正在規劃退休後要做些什麼事情。大部分時間我會投入在台美生技協會或 TID 臺灣新藥聯盟的一些志工工作,那除此之外,我覺得很值得把以前的職涯記錄下來。因為我也常常跟年輕人聊天,想說除了可以一對一幫助一兩個人,如果能把過去的經驗記錄下來,就能造福更多人。
當初我以為我的受眾會是在美國的臺灣生技人,可是事後透過臉書分析才發現,大部分的追蹤者都在臺灣。從留言中我也看得出來,大部分的人也不是做生技產業的。所以後來,除了職涯相關的內容,我也開始加一些生活面的東西。不過最初的出發點,還是希望能給在美國的生技人一些職涯的經驗分享。
Harvey: 很有趣,好像常常會這樣,一開始設定的目標族群,跟最後真正看的都不是同一群人。很多人好像也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職涯中影響深刻的一句話:不要讓人占便宜
Harvey: 我想我們的聽眾也很關心職涯發展。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回顧你的職涯,有沒有哪一句話,或是哪一個人對你說的話,對你影響特別深?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當時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聽到的呢?
二姐: 有一句話是我博士指導教授對我說的,我一輩子都會記得。
我的博士指導教授在賓州大學,她後來被譽為美國的基因治療教母,名字叫 Katherine High。她是 Spark Therapeutics 的創辦人,那家公司是全美第一個拿到 FDA 藥證的基因治療公司。
當時我已經離開她的實驗室,拿到博士後的機會,去了另一個實驗室。不過因為還在 賓州大學,所以我們還是常常會一起吃午飯。有一次我抱怨我的博後老闆剝削實驗室很多人,例如一些波蘭來的博士後研究員,只拿到非常少的薪水。當時,她看著我,跟我說:「筱玲,如果你讓人家占你便宜,那你也活該。」這句話對我後來的人生與職涯影響非常深。
她是一個典型的女強人,非常重視的一點就是,你一定要保護自己的權益,不要讓人家占你便宜。她的意思是,這些被剝削的博士後可能有他們不得已的原因,例如真的非常想來美國等等,所以才會在某些情境下被人利用。
我後來在職涯上,真的學到說,很多事都必須靠自己去談、去爭取,不能再以臺灣那種想法:「我好好表現,人家就會賞識我。」在美國這樣的環境,這幾乎是不會發生的。我常說,人們會做那些,他們做了也不用付出代價的事。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怎麼保護自己的權益,很多事情本質上都是一個談判的過程,不管是跟上司還是同事。這句話,「不要讓人家占你便宜」,我真的一輩子記得。
她後來達到很高的成就,我覺得這也是有原因的。我當年跟著她的時候,她還只是助理教授,而我是她第二任研究生。現在回頭來看,她的成功是有跡可循的,她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Harvey: 這句話我也很有感覺。以前我們會覺得把手上的事情做好,總是會有人看到,或者會有人幫忙伸張正義,所以不要自己出來爭。但在美國的職場上,完全不是這樣。如果你有做什麼事,沒有講出來,沒有人知道你做了什麼。反而很多人沒做什麼事卻一直講,結果在職場上獲得的資源比默默做事的人更多。所以溝通能力真的非常重要。
職場上溝通與爭取的重要性
Harvey: 筱玲姐,你在職涯旅程中,有沒有遇到某個時刻,讓你真的體會到「溝通很重要,而且必須自己去爭取」?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具體的例子嗎?
二姐: 我後來進入法規工作之後,才真正深刻體會到這件事。
法規是一個非常重視溝通的領域,相較於研發,它幾乎整天都在處理溝通的事情。因為你經常需要和不同部門對話,確保整個藥物開發計劃有一致性,並且清楚知道什麼時候該和監管機關進行討論,以及在什麼時間點要取得共識。並且這個工作除了要跨部門溝通,「向上溝通」也非常重要。為了保護自己,你必須和老闆密切討論你的需求與想法。
在美國的職場環境裡,大家會期待你是透明的。很多事情必須講清楚,才能創造出雙贏的局面。因為你不會知道什麼事情對對方來說是重要的,而你自己在意的事情,也必須清楚表達出來,讓同事和主管都能了解。這真的非常重要。
從學界到業界的轉折、從研發到法規的轉折
Harvey: 剛剛筱玲姐其實有提到,後來決定從研發領域轉到業界。我很好奇,當時是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很多讀博士的人的目標都是要走教職。可以談談你當初是什麼契機,讓你確定不留在學界,而是轉向業界嗎?
二姐: 我覺得我的經歷其實會有點女性視角。我的職涯中有兩個非常大的轉折點:一個是從學界進入業界,另一個是從業界的研發轉到法規。
作為一個妻子和母親,我最大的限制其實是地理位置的限制。我不能隨意到其他地方找工作,必須選擇一個家人能接受的地點,讓我先生和小孩可以好好生活。而這大大限制了我能選擇的職涯路徑。
這兩次轉折,其實都是因為失業。第一次,是因為我沒有拿到教職工作。那時候我做了六年的博士後研究,但始終沒有拿到教職,又因為家庭因素不能到外地任教,所以最後請以前的學弟幫我介紹,進入一家生技公司從事研發工作。第二次轉職,從研發轉到法規,也是因為失業。那家公司後來資金用完,營運出現問題,我因此失業了將近兩年。
失業的那兩年,雖然對職涯是一種挫折,但因為小孩還小,其實對家庭來說是好事。那時候小孩還在幼稚園、一二年級,我有兩年的時間能陪伴他們成長。同時我也利用這段時間到 Temple University ( 天普大學 ) 念法規碩士,並在那裡透過一位同學介紹,找到我第一份法規的工作,進入 Teva。
Harvey: 為什麼當初會選擇念法規呢?
二姐: 其實我不是原本就特別有興趣,而是失業時我做了很多嘗試。
一方面我有繼續找研發相關的工作,但我發現如果在小公司做到資深研究員或副主管等等,要平行轉換到大公司非常難。像我去 JNJ 應徵研發的職位,頂多也只能回到資深研究員的職級,甚至更基層的職位。再加上我不能搬家,選項非常有限。
所以我那時也在探索其他備案,比如考證照、看看要不要轉去做臨床研究助助理或是去學習軟體、改行做統計分析。最後,我是覺得法規這個領域特別吸引我。因為法規的工作需要對整個製藥流程非常熟悉,從藥品如何製造、臨床前的數據需求,到進入臨床試驗之後的要求,到最終如何申請藥證,每一個環節都要理解。它讓我能夠看到非常廣的視野,同時出差需求又很低,大概一年去兩三次 FDA 開會而已,對我來說非常合適。當時其實我還有在持續找研發的工作,只是沒找到理想的職缺。最後剛好是法規領域的機會先出現,所以我就進入了這個產業。
Harvey: 我對你剛剛提到的「地理限制」這點特別有感觸。我們頻道常鼓勵大家多出去看看世界,但當人到了三、四十歲,有了家庭之後,現實生活中的限制自然會浮現,很多選項就會被限縮。
但很多時候回過頭來看,會發現這些限制反而帶來了新的可能,是原本未曾想過的路。我覺得筱玲姐你的經歷就很符合這樣的轉折。
製藥法規工作的日常
Harvey: 很多聽眾對於製藥法規在藥廠的角色可能不是那麼熟悉。能不能請筱玲姐簡單介紹一下,平常一天的工作主要都在做些什麼?
二姐: 製藥法規的工作,主要就是代表公司與監管機關打交道。整個製藥流程中有兩個非常關鍵的門檻。
第一個門檻是「進入臨床」。在藥品進入人體試驗之前,必須先有大量數據,包括藥品的品質標準、品質控管,以及臨床前的動物試驗或體外實驗數據等等。這些資料必須說服 FDA,讓他們認為這個藥是安全的,才會同意進行人體試驗。在美國,這個程序叫做 IND ( Investigation of New Drug 新藥研究 ),在美國以外的地區則通常稱為 Clinical Trial Application ( 臨床試驗申請 )。
第二個門檻是「臨床發展過程」。從第一期、第二期到第三期的臨床試驗,以及後續的製程放大,每一個階段都必須和 FDA 密切討論。這包括臨床試驗的設計、受試者群體、終點指標等,以確保最終能達到 FDA 所要求的「Substantial Evidence of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 充分的安全性與有效性證據 )」。
所以,法規的工作需要非常熟悉 FDA 的官方指引和先例,同時也要整合公司內部不同部門的資訊,要了解研發、製造、臨床發展各部門的進度,然後判斷什麼時間點應該主動與 FDA 溝通、安排會議、取得共識等等。
整個製藥過程中,最昂貴的階段就是臨床試驗。一個大型試驗動輒上億美元的投入,如果沒有事先與 FDA 在試驗設計上達成共識,是不應該輕率啟動的。這不僅是財務風險,更可能導致整個藥物開發計劃被延遲甚至失敗。
有經驗的法規人員,能夠根據手上已有的數據,判斷現在是否已經具備與 FDA 進行建設性討論的條件。如果資料尚未成熟,FDA 有時甚至會直接拒絕開會。
我常常比喻說,我就像是導演、各部門是演員,而我們的目標是在 FDA 面前演出,讓我們的藥最終可以順利上市。
適合法規工作的性格特質
Harvey: 筱玲姐,你覺得你在性格或人格特質上,有哪些地方特別適合法規這個工作?大部分人聽到「法規」,感覺就是照表操課、比較制式化。但我覺得你是少數聊法規,會整個神采奕奕、覺得很有趣的人。你覺得自己性格中有哪些特點,讓你後來發現自己蠻適合做這件事?
二姐: 剛開始我也不確定我是不是適合這份工作,但進去做了之後,發現自己能駕馭這件事情。大家對法規「照本宣科」、「制式化」的印象,通常是因為看到例如外商公司在臺灣要交藥證的狀況。那種情況下,整個藥品的研發計劃已經是很確定的,那法規的工作真的就只是把資料整理成監管機關需要的格式。
但如果是在美國或歐洲做法規,很多東西是從零開始建立的。你對藥物完全陌生,連臨床試驗要怎麼設計、怎麼運作都還不知道,因此這個過程其實非常有趣。你必須幫助公司決定資源應該投放在哪些地方,才能最終取得監管機關的同意。這種工作在公司裡的能見度是很高的,通常帶臨床開發的副總去跟 FDA 一起開會,甚至在小公司裡,是要親自帶著 CEO ( 執行長 ) 去跟 FDA 開會的。我覺得我大概也蠻喜歡那種注意力的。
另外,做法規還需要非常良好的口條。我覺得我的優勢是,我從小口語表達能力就不錯,高中時在北一女,中英文演講比賽都有得獎。如果本來就是一個講話有系統的,換一個語言來溝通其實沒有太大差別。
Harvey: 真的很有趣。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把法規工作形容成「導演帶演員去開會」。仔細想想其實很合理,因為新藥開發最重要就是要通過 FDA,法規人員等於是掌握關鍵的角色,要能協調各部門的配合,才能推動整個流程。
從國際法規開始的轉職過程
Harvey: 那筱玲姐,你一開始從研發轉到法規,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挫折?畢竟研發和法規的差異蠻大的。
二姐: 我其實蠻幸運的,因為剛進入法規領域時,是從「國際法規」開始做起。國際法規相對壓力比較小,因為在大型藥廠裡,「國際法規」指的是美國與歐洲以外的市場。而美國是全球第一大市場,歐洲是第二大,這兩塊是整個公司的重心所在,所以高階主管會非常關注,法規團隊的壓力自然也很大。但國際市場通常只佔全球營收的 10% 左右,對於整體業績影響比較小。所以除了你的直屬主管,幾乎沒有人會特別盯著你。
Harvey: 所以你是先從國際法規切入,壓力相對較小。那後來公司內部是不是有一些職務上的轉換?
二姐: 對,我在國際法規部門做了四年,後來部門改組,公司希望我搬去新加坡,甚至幫我女兒安排好了新加坡的美國學校。但我其實不想離開美國生活,於是趁這個機會,在 JNJ 內部積極尋找其他工作機會。
當時我運氣也不錯,找到了兩個 JNJ 美國法規部門的職缺,一個在免疫部門,另一個在癌症部門。這些機會其實是我在做國際法規期間,跟美國法規部門的人打交道,慢慢建立起人脈的結果。所以後來等於是重新申請進入美國法規部門。
進入美國法規部門之後,我覺得很有意思。因為美國法規很多時候需要從零開始設計整個藥物開發計劃,不像國際法規那樣只是根據公司對歐美的政策做調整。美國和歐洲的監管機關對藥證的要求是全球最嚴格的,所以科學上的挑戰性也大很多,而我蠻喜歡的。
下一站職涯:從 JNJ 到 BMS 的關鍵轉職
Harvey: 那筱玲姐你做了這個轉換之後,在 JNJ 總共待了多久?
二姐: 我在 JNJ 一共十年,其中四年在國際法規,六年在美國法規。
不過後來和當時的老闆處得並不是很好。在大公司裡,一旦升到主管,下一步要升到資深主管就比較困難。我曾和副總討論過自己的升遷路徑,而他告訴我,必須先去做早期開發階段的全球法規業務,等於是一條很長的路,才能升上資深主管。
所以當 BMS 的一位招聘官來問我,要不要去做資深主管的職位時,我想那條路比較快,就決定跳槽了。
Harvey: 在藥廠裡,好像真的都是跳槽升職比較快。
二姐: 對。所以我就去了 BMS。
我去 BMS 負責的計劃非常有意思,是做他們的 OPDIVO® 的非小細胞肺癌的案例。OPDIVO® 是他們一種 anti PD-1 ( 抗 PD-1,用於癌症免疫治療 ) 藥物,是公司最重要的專案,所以挑戰性很大。
我很開心的加入了 BMS,而且 BMS 離我家只有 20 分鐘的車程,比起之前在 JNJ 要開一個小時快很多。
Harvey: 這聽起來有點隨機,招聘官找到你,你就接到了這個機會。你本來也沒有特別去找吧?
二姐: 對。而且其實做法規,招聘官常常會來找,只是我平常都不會接他們電話。那天我大概是和老闆有點不愉快,所以就接了那通電話,結果就開啟了這個機會。算是蠻幸運的。
而且我去 BMS 的過程也有點戲劇化。當時我手上有一個新藥的申請,FDA 正在審查。那年二月 BMS 錄取我,我說這個新藥沒拿到之前我不會離開。所以 BMS 就等到我新藥申請通過的那一天。那天我把辭呈從抽屜裡拿出來,當天就辭職了。
職涯上的貴人
Harvey: 那我想問,你在這些轉職過程中,有沒有哪一位貴人,是你特別感謝的?甚至覺得後來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他的栽培?
二姐: 有的。我在 JNJ 的第一位老闆就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貴人,他對我有幾個方面的重大影響。
首先,在那之前我基本上是研發出身,個性比較書呆子。但法規這個工作其實是一個商業職能,需要跟很多部門溝通,甚至要能影響別人的決策。他在這方面給了我很多幫助。
第一,他會帶我去「拜碼頭」,去認識其他部門的副總。對我這種比較內向的人來說,這其實蠻不自在的,但他會鼓勵甚至「逼」我去做。第二,他還幫我請了一位一對一的高階主管教練,從說話的語速、開會時的姿態,到如何讀懂會議上的氣氛,都進行了全方位的訓練。我想可能我和他蠻投緣的,所以他願意在我身上投入這麼多資源。這對我後來的發展,真的有很深的影響。
我後來去北美法規的時候,也沒有讓他覺得很尷尬,因為他剛好要退休了,所以時間點上非常完美。
Harvey: 他有沒有什麼事蹟或是跟你講的一句話,讓你印象很深刻?
二姐: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我去面試的時候,他居然拿出 JNJ 的 credo ( 信條 ) 來跟我解釋。他就講說,JNJ 的第一個責任是對病人,然後一層一層,第二層是對我們的公司員工,接著是對社會的責任等等。
我當時心裡覺得:「也太可笑了吧!你真的相信這一套嗎?」結果後來跟他共事之後,我發現他真的相信這一套。雖然我不敢說公司裡所有人都相信,因為很多時候總是存在一些灰色地帶,你會覺得公司可能還是會以自身利益為優先。但我很確定,我的老闆就是這樣相信這一套的人。所以他才會在面試的時候,花時間解釋 JNJ 的 credo。
Harvey: 我也從來沒聽過有人這樣做。真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老闆。
剛剛筱玲姐分享了在職場上遇到一位值得學習而且很照顧自己的前輩。很多人其實都會希望能遇到這樣的導師,或者我們常說的「貴人」,一路提攜自己往上走。那你回頭看職涯,覺得這件事是純靠運氣嗎?還是說,其實也有一些地方是可以靠自己主動爭取的?能不能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些小技巧?
二姐: 我覺得運氣很重要,但有些事情還是要靠自己去經營。
像我剛剛提到的第一位貴人,那真的就是運氣,因為他剛好就是我的老闆。
不過,在他帶我出去「拜碼頭」的過程中,我也主動經營其他關係,尋找能夠提供價值的機會。比方說,我會問對方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地方,然後請他們給我一些回饋,像是在會議上我的表現有哪些地方可以改進。所以後來,他們都很樂意幫助我,甚至到後來我想轉去北美部門的時候,他們也幫我寫了非常好的推薦信,讓我成功進入新的單位。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看到我真的有「growth mindset ( 成長心態 )」。他們給我的建議,我都虛心接受,並且實際付諸行動去改變。對他們來說,這也是一種成就感。而且像 JNJ 這樣的大公司,他們在目標與績效指標上,就算是高階主管,也需要交代自己培養了哪些人、在人才發展上做了什麼。所以當我努力成長的同時,也是在替他們加分。
很多年輕人可能會覺得:「這些副總裁這麼忙,我去打擾他,他一定不高興吧?」但其實不一定,因為人才發展本來就是他們的績效之一。所以在職場上,這其實是一個互相幫忙的過程。
Harvey: 我覺得這很有趣,很多人其實不知道,越到高階職位,「帶人」反而是績效指標之一,所以這其實是一種互相幫忙的關係。
我覺得剛剛筱玲姐提到一個很關鍵的點:如果貴人給了你建議,他必須看到你有實際的行動改變,才會願意繼續幫你。畢竟講一個建議可能只要十分鐘,但你怎麼實踐、怎麼改變,才是關鍵。
我自己觀察到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就是跟幫助你的人主動回報。如果你幫助了一個人、和他聊了半個小時,之後每個月都會收到他的信,說上次的對話讓他學到了什麼、他如何去實踐等等,這樣的人會特別讓人印象深刻。
如何讓貴人願意幫你
Harvey: 筱玲姐,那你在職涯中帶過一些人,有沒有遇過哪一類人,讓你覺得值得多提拔?他們做了什麼,讓你願意多花心力在他們身上?
二姐: 有啊,其實不少。很多年輕人會來跟我請教職涯建議,如果問完就消失,當然效果很有限。不過就像你剛剛講到的,如果他們之後有再回來告訴我他們的進展,就會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但當然也要注意互動的頻率,不能太頻繁。我覺得三個月或六個月回來講話一次會比較合適。如果每週或每月都來,反而會讓人覺得有點負擔。
我覺得我看到的這些讓我覺得「發光發亮」的人,通常有幾個共同特質:他們能夠清楚表達自己對未來的願景,也能把我說過的話重新整理、重新表達,然後說出他們打算怎麼去行動,這樣的人會讓我感受到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有主見。
Harvey: 這很重要,統稱叫做「職涯方向感」或「人生方向感」,感覺知道自己大概要往哪邊前進。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特質。我和很多人互動過,有方向感和沒方向感的人,差別非常明顯。
簡單來說,就是他是被自我驅動,還是是被外部推動的,例如是因為某某人叫我這樣做,我才這樣做。相對的,也有人會是因為在打造自己的職涯,所以現在選擇去累積這段經驗,因此在做這件事。
這兩種人,可能短期內看起來在做一樣的事,但因為背後的方向感不同,未來的發展路線就會完全不一樣。我覺得這很有趣。在職涯初期可能還看不出來差異,因為大家處在類似的環境與時間點。但往後走,就會開始明顯分歧,各走各的路。
二姐: 對,我也有這種感覺。而且我發現,我替年輕人諮詢的時候,他們比較傾向說「我做了哪些事、得到什麼成就」。但隨著我年紀漸長,我現在更常會問:「你自己覺得,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因為我認為,有些事情對我來說重要,不一定對你來說也一樣重要。每個人達到自我實現的路徑都不同,也不一定每個人都適合同一種方式。我會更想聽到他們去描述他們真正追求的是什麼、個性適合做什麼,這其實就是一種自我分析的過程。對於那些清楚了解自己優勢與劣勢的人,我通常會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升遷爭取與臺美升遷文化差異
Harvey: 那筱玲姐,你在大藥廠經歷過幾次升遷,有沒有哪一次是你主動爭取來的?比如說你自己跟主管說:「我覺得我經驗差不多到了,我想承擔更大的責任,能不能給我這個機會?」還是大多都是你表現很好,然後別人就幫你升職?
二姐: 我以前會比較被動一點。不過我在粉專寫過,自從有一次我被人家「向上管理」之後,看到那些非常積極的美國人是怎麼做的,我才開始轉變。他們通常會直接對老闆說:「老闆,我現在做的是這些工作。我要做什麼才能升到下一層級?」意思就是想要一份明確的清單,只要我把那些事情做到,你就不能不升我。所以我後來很多升遷的過程,都是靠這種明確的溝通方式。我會直接問老闆:「你希望我做到什麼事情,你才會覺得我準備好升上下一個職等?」
其實 JNJ 有一份「competency table ( 能力表 )」,裡面會很明確的列出,作為一個經理人應該能獨立處理哪些情境、應對什麼場合、制定哪些策略。每一個職等需要哪些能力,都有清楚的定義,而且需要達到專精的程度,才有資格晉升。所以在每次一對一會議的時候,我就會把這張表拿出來討論,說:「這一條我覺得我做到了,你覺得呢?」如果老闆覺得還不夠,我就會虛心請教:「那我要怎麼改進?」
很多事情其實都是可以主動爭取資源的。尤其在大公司裡,有很多領導力訓練課程可以選擇。例如老闆說你要加強溝通能力,那你就可以去報名參加國際演講協會來訓練自己。我以前帶領下屬時,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鼓勵他們接下有挑戰性的任務。先嘗試做一些下一個層級的工作內容,這樣當我幫你爭取升遷時,就有實際的證據可以說,這個人已經準備好了。
Harvey: 這真的很有趣。我們也和臺灣主管、臺灣老闆聊過這類的話題,但這樣的情況在臺灣職場真的比較少見。但在美國,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大家如果想要什麼,都會直接講出來,並且要求對方清楚列出標準,達成之後就能往下一步前進。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文化差異。
二姐: 對,我有時候也在想,會不會是因為美國的機會真的比較多。我以前當主管時,和一群同階層的經理人一起討論下屬表現時,常常會提到一個問題:「這個人是不是有可能離職、可能跑掉?」如果某個人表現很優秀,主管當然會擔心他跑掉,因為美國的外部機會太多。所以主管需要非常明確的告訴表現好的員工,他做到哪些事情、證明哪些能力,就可以往下一階段邁進。這樣員工也才知道該朝哪個方向努力。同時,主管也要設法用一些誘因來把人才留下來,因為優秀的人在外面一定也有機會。
Harvey: 對,所以當主管也真的不容易。在美國開公司也不容易,不過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下次可以再聊。
面對職涯低潮的心境調適
Harvey: 最後再聊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問題。筱玲姐剛剛很雲淡風輕的講到,自己人生中經歷過幾次失業。那我想是事後回顧才可以雲淡風輕的說,當下一定會有一些低潮期。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心境轉變的方法,或者你自己曾經用過的一些方式,在面對職涯低潮時特別有幫助?可以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嗎?
二姐: 我覺得,身為一個妻子、一個母親,當職業上不順遂的時候,通常可以想:「我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多花一些心力在家裡、在小孩身上。」對我來說,所有事情都有好處跟壞處,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好,也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壞。事情發生的當下,我會試著去想,它的優點是什麼、缺點是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要用很平衡的方式去想說:「哪些事情是我能掌控的?哪些是我不能掌控的?」像今天我失業了,因為外面景氣不好,這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但我能掌控的是什麼?我最近有寫一篇文章,也提到這個主題,如果你是新鮮人,或是正在失業的狀態,應該要怎麼樣儲存能量、吸收新知,怎麼去了解外面有哪些工作機會,以及大家現在在找什麼樣的人才。這些,都是我可以掌控的,是我可以投資在自己身上的部分。
所以,在心情調適上,只要每天都覺得有進步、有好好投資在自己身上,我覺得就是一種很正面的心理建設。
Harvey: 這個超棒。真的很多事情就是沒辦法控制。
我最近跟很多人聊到這個話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COVID。我記得疫情發生前,各種公司、機構都有未來的規劃、預估明年的成長率等等。但 COVID 一來,全部都不準了,沒有人能預料到。很多變化根本不在我們的掌控裡面。
二姐: 對,而且那也不一定完全是不好的事。
COVID 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後來我跳槽去 Ambrx,完全遠端工作,公司在 San Diego。因為那時候大家都遠端工作,所以反而拓展了很多工作機會。
我去 BMS 兩年,離開的時候我那個部門大概流失了 17 個人,因為大家都跑去做遠端工作。突然所有公司都接受遠端工作,只要不是實驗室操作為主的工作,就出現了非常多新的機會。
Harvey: 這又呼應到剛剛說的,事情都有優缺點。
台美生技協會的角色與特色
Harvey: 那最後,筱玲姐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台美生技協會?我前陣子有去那邊分享過,但可能很多聽眾還不太熟悉。你現在是現任會長,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嗎?
二姐: 好啊。
台美生技協會某種程度上有點像是玉山協會和 BTBA ( Boston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波士頓臺灣人生物科技協會 ) 的合體。美國有很多地方性的 BTA ( 台灣生技協會 ),像是波士頓、南加州、北加州、德州等,但那邊多半以學術界為主。
那台美生技協會,我們的據點和大部分幹部都在三州都會區,也就是 New Jersey ( 紐澤西州 )、Pennsylvania ( 賓夕法尼亞州 ) 和 New York ( 紐約 ),這裡的成員則比較偏向業界背景。這個區域的特色是以大型藥廠為主,雖然創新能量不如波士頓那麼蓬勃,但工作相對穩定,而且可以學到完整的藥物開發流程,包括製程放大、大型臨床試驗設計等中後期的經驗。在三州都會區,這類機會非常多。我們大部分的幹部來自這裡,也有一些來自加州。雖然也有學術界的志工參與,但協會重點並不在學術,而是在產業實務。
我們每年會舉辦年會,像今年很榮幸邀請到 Harvey 來分享。年會是一個讓全美各地對業界有興趣的臺灣生技人齊聚一堂,討論最新議題。今年第一天的主題包括 AI 在製藥上的應用,以及目前非常熱門的 Antibody Drug Conjugates ( 抗體藥物偶聯物 );下午則有分組討論,讓大家深入交流職涯相關的話題。除了年會,我們平時也會舉辦小型聚會,比如在 D.C. ( 華府 )、Pittsburgh ( 匹茲堡 )、紐約等地,幫助當地的生技人建立連結、了解彼此需求。
我覺得台美生技協會最大的特色,就是由很多有實戰經驗的臺灣生技人組成,在美國提供經驗傳承,幫助還在努力中的年輕一代。相較其他組織,我們有更多業界資深的幹部,這是我們很大的優勢。
Harvey: 我覺得現在臺灣年輕人再出來,真的越來越幸福,因為有很多像筱玲姐這樣的前輩,願意分享經驗、提供指引。
如果有聽眾朋友想加你 LinkedIn,應該沒問題吧?
二姐: 對啊,沒問題。
Harvey: 另外,前面也提到你有一個粉專「退休生技二姐在美國」,大家也可以去追蹤。我自己也很喜歡看上面的文章,很有啟發性。
今天非常感謝筱玲姐花時間和我們聊一聊。如果聽眾朋友還有後續問題,我會再轉達。
二姐: 謝謝你,也謝謝今天有這個機會,讓我能和大家線上見面。